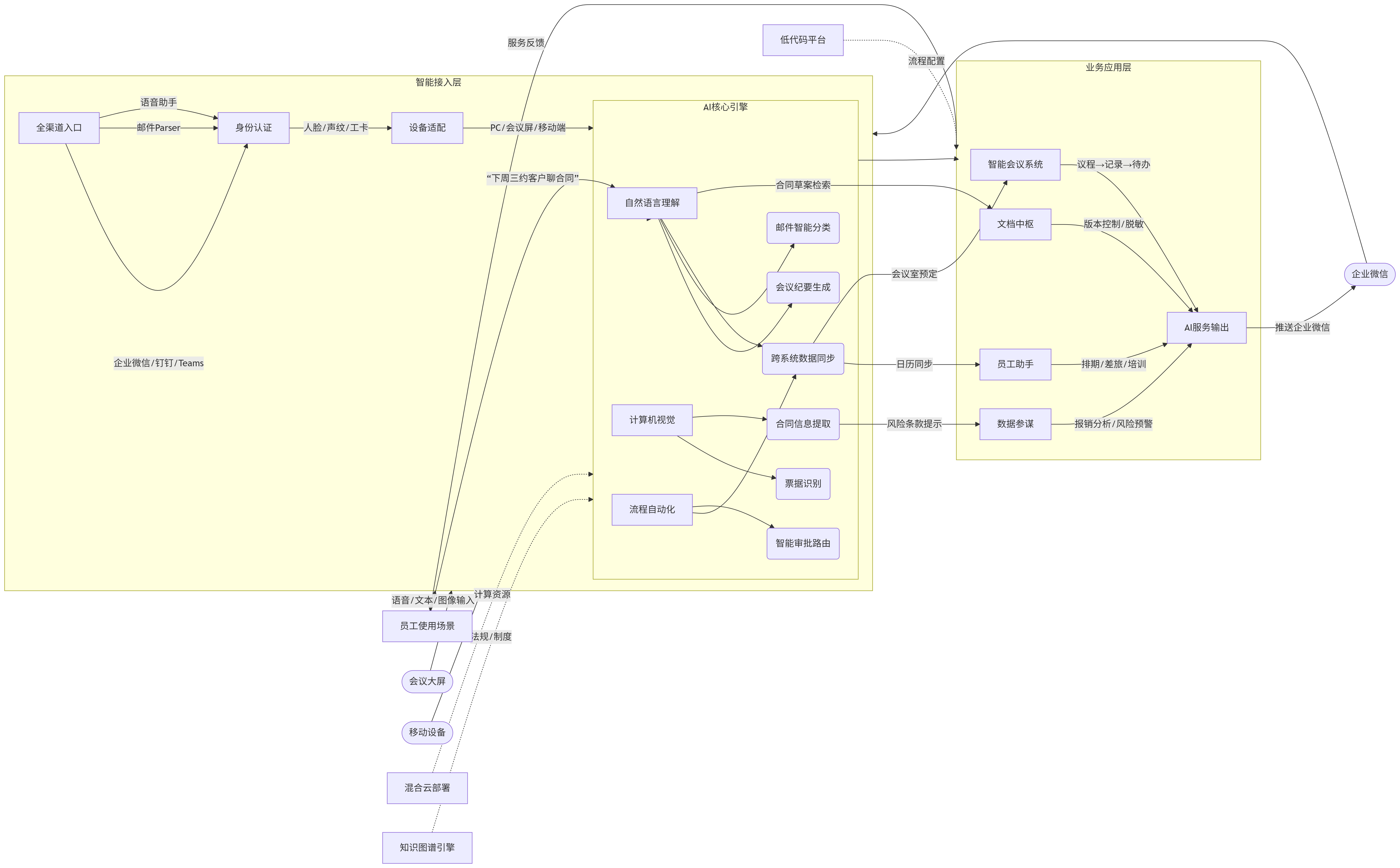操场变形记
操场变形记
CanYum操场边的柳絮开始作乱时,我的脂肪终于到了不得不剿的地步。那件三年前的牛仔裤,如今套在身上,活像给火腿肠包锡纸,稍一弯腰便发出哀鸣。
晨跑的大学生从身旁掠过,运动鞋踩着《本草纲目》的节奏。我喘如风箱,汗珠子砸在塑胶跑道上,竟能溅起些微尘烟。有个穿荧光绿运动bra的姑娘,每周二四六准时出现,马尾辫甩动的频率,与我心跳监测仪上的数字总呈正相关。
篮球场最是欺生。那些十八九岁的精瘦猴子,能在空中做出各种违背地心引力的动作。我试着抢篮板,膝盖却发出类似老式木门转动的声响。球没接着,倒接住了场边女生”大叔小心”的惊呼——原来我比想象中更早获得了这个尊称。
体育系王教员常来巡视。他捏着我肚皮说”脂肪层超标15%”,手法与菜场大妈掐茄子老嫩无异。后来送我张训练表,纸上的配速要求,看着像某种古代酷刑的说明书。
最是那台体重秤狡黠。明明晨起时已降了二两,夜跑后再称反增半斤。后来才知跑道边新开了奶茶店,每次”奖励自己”的烧仙草,都暗中标好了卡路里的价码。
暮春的晚风路过操场时,总捎带些嘲笑。把胖子的喘息声、篮球砸框声、体测仪器的滴滴声,搅拌成一杯名为”中年危机”的冰沙。唯有那件晾在单杠上的速干衣,在月光下静静滴着水,像面投降的白旗。
评论
匿名评论隐私政策